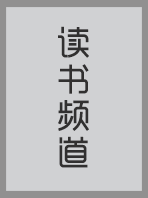第五十三章 迁徙
经过长达数日的远途跋涉,斯坦穆中部的希斯坦布尔行省逐渐在地平线上现出了轮廓。
斯坦穆不比其他大陆诸国,行省之间的交界处往往存在着极为辽阔的平原草地,渺无人烟。惯于迁徙的游牧民族自然不会认为距离是个问题,但是相对于沦为难民的他们而言,双腿已经成了最后还能依靠的东西。
所有从北部逃出的难民当中,很少还有人能留下马匹或是别的什么牲畜。从财产到勇气,这场战争几乎耗尽了斯坦穆人的一切。
战火就在后方十余里的城池内熊熊燃烧,随着风势自北而来,逃亡中的人们仿佛再次嗅到了那股浓烈的血腥味。不算太长的日子里,从边境直到国家中部,一个又一个行省被相继攻破。愈卷愈是庞然的难民浪潮由最初的数千不到逐渐扩展为十万有余,行动迟缓的同胞都变成了蛮牙人腹中的美食,于是幸存者们也就更加惶恐失措,宛如一群盲目奔逃中的牛羊。
巴帝主力军队的反攻,使得蛮牙锋线的推进速度开始转缓。几番鏖战之后,希斯坦布尔便成了分隔斯坦穆南北端的最后屏障。一边是尸骸遍野的死地,一边则是处在惊惧气氛中的战栗家园,没有人能预料希斯坦布尔什么时候也会变成一堆焦桓废墟,但绝大多数北方难民赶往的首选避难所,赫然便是这座孤独屹立在战线前沿的行省。
突兀回拢的地势与草原上盘旋斜戈的运河,注定了希斯坦布尔成为去向国家南部的必经之地。很多身处不同行省的远亲在逃亡途中相遇,在感叹命运反覆无常的同时,其中部分豪绅家族便结成规模较大的队伍同行。即使是到了如此凄凉窘迫的境地,他们依旧还竭力保持着贵族做派,那些已不多见的马匹和满盛着金银皮裘的行囊,也从另一个方面令他们的自视更高。
已经极少有人能剩下些什么了,穷鬼们甚至连每顿饭的着落都难以寻获。在延绵无尽的难民人流中,像这样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逃亡者占了八成以上比例。他们携家带口,茫然随着身边人群迈动脚步,逆来顺受的本性让各种负面情绪都保持在理智的水平线下。同为难民,穷人唯一还在乎的就是能不能活下去,仅此而已。
苏萨克的残党和地行族人,也悉数混在浩浩荡荡的逃亡大军里,向着希斯坦布尔的边关城门进发。早在离开驻地的时候,索尼埃就已经下令舍弃了所有马匹。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他都不觉得再次拒绝撒迦的建议是个明智举措。
事实上那名并不善于言辞的年轻人偶尔提出的观点往往直接而有效,正因为如此,索尼埃才会直到今天还处在深深的悔恨之中——如果在早些时候不那么刚愎自用,或许现在那些粗豪部下都还活得好端端的,就像以前那样。
解下武装与红巾的苏萨克,看上去和普通人并没有明显的不同。三五成群混迹于人流里的地行侏儒虽然稀稀拉拉延伸了将近数里的范围,但他们才是撒迦心中真正担忧的症结所在。
由于种种必须去考虑的安全因素,希斯坦布尔的城关只开了一道偏门。狭窄的出入空间配备着极之森严的警戒盘查,明晃晃的刀枪环侍下,每次得以通过城门的难民数量,不超过两人。
十个,一百个,甚至是一千个地行侏儒从城关守军眼前经过,或许都不会引起过多的注意,但撒迦需要考虑到的人数,却是整整六万以上。这些草原上并不多见的矮小生灵无法再依靠掘洞潜入,因为眼前的这座行省不比摩利亚帝都,在城墙后面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很可能都已经人满为患。
“在有些特殊的时候,黑暗要比阳光招人喜欢的多。”尽管仍未消肿的嘴唇在说话时有些麻木,全身焦灼的伤处也还在隐隐作痛,但戈牙图的神态却是飞扬跋扈的,“交给我,小子,你会惊讶地发现老师还有很多杀手锏。当然了,我的小豌豆,这只是为你而做。”
默然前行的人群中,一袭黑袍的撒迦微微摇头:“就算是晚上也没有可能,我们得想个别的办法。”
对地行掘进过分旺盛的自信心,让戈牙图一直不认为撒迦正在担心的问题是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缩手缩脚了?我们不需要钻出地面,而是透过土层就能闻出一里以外蹦达的究竟是条精力旺盛的野狗,还是他妈的趴在巷角墙边挨操的婊子!当初不正是因为这个,我和我的族人才能在皇宫里找到你的吗?听我说,最保险的方法是你也一起下到地底去。如果有人发现的话,我想除了普罗里迪斯那样的怪物,这世上不会再有什么东西能在你的手底下保住小命了,不是么?”
撒迦跨出地面上深深凹下的硕大泥坑,空气中弥漫着新鲜土壤特有的腥味,始终在固执地沁入他的鼻端:“如果只有我和你,或许我会按你说的去做。可是现在,我只想能够低调些进城,然后安顿下来,至于你的计划,那恐怕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样说,你应该是有了自己的想法?”戈牙图显得有些泄气。
“让索尼埃和他的人先进去,听说他们能找到些有用的朋友。”撒迦掠了眼后方,那片天空的阴云底部,正闪耀着火一般的赤红,“这是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没有利益的时候,我们最好还是避开它。”
戈牙图思忖半晌,挥手叫过一名诚惶诚恐的族人,接过对方递上的干粮狠狠啃了一口:“好吧,我承认你说得不错。不过话说回来,撒迦,你难道不认为我们的新朋友有点缺乏价值观念?我的老天,他们宁愿随身带上这堆一文不值的猪食,也不肯把那些金灿灿的宝贝儿从山谷里搬出来......”鬼祟地环顾着周围,地行之王压低了声音,“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藏着多少钱,但我发誓,那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得多。”
撒迦略为讶异地看着他:“我以为你最感兴趣的不会是金钱。”
“当然不是金钱,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戈牙图恼怒地低声吼道,“我只想得到那个妞!”
“所以我们得尽快想办法进去,裁决和溯夜一族,可能已经在南边的某个地方了。”撒迦忽转过视线,望向侧方径直行来的一个窈窕身影,“如果你还想活着见到海伦,现在最好找个地方躲起来。”
“为什么?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一位无畏的勇者低头!”戈牙图气咻咻地顺着对方视线望去,立时触上了罗芙投来的冰冷眼神,“呃,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情要做,小子,恐怕我得先离开一会儿了......”
“能告诉我,那天晚上你到底用了什么吗?”撒迦叫住了准备溜之大吉的侏儒。
戈牙图略顿了脚步,不安地回顾着,这几天来他感觉自己像个无力抗拒任何事情的婴儿,而扮演神甫角色的罗芙则用电系魔法洗礼了他的全身:“那小玩意叫‘迷乱水晶’,盐湖盆地的特产。怎么说呢,除了强烈的催情效果以外它没有任何作用。如果你想要,我这里还有很多。”极为暧昧地挤了挤眼,侏儒飞快钻进人群,“不过,我想你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了。”
撒迦苦笑着摇头,直到那熟悉的清香气息逐渐靠近,方才若有所思地转回身,执住罗芙的柔软手掌:“别再为难戈牙图了,他可不会什么魔法防御,迟早会变成烤肉的。”
罗芙的颊边悄然飞起两抹嫣红,先前雌豹般凶悍的眼神已变得羞不可遏:“这下流的侏儒,迟早有一天我会杀了他。”
“你最好还是别这样做,戈牙图是我目前唯一还能找到的老师了......”撒迦半开玩笑的接口。
“喂,年轻人,身边的妞不错啊!大家轮换着玩几天?”后方赶上的马蹄声低促响起,一个体态肥硕,留着细长八字须的青年男子在数十名随从的簇拥下分开人流,驾驭坐骑缓缓行到撒迦旁侧,“放心,我不会白玩的,要钱还是要个官衔你尽管说。等进了城,我保证你能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我们汤姆森少爷可是斯坦穆最大领主唯一的继承人!”几名随从争先恐后地附和着,仿佛早已习惯于应对类似的情形。
撒迦按住了罗芙悄然抬起的右手,微笑道:“如果我不愿意呢?”
四面八方的人群间,无数地行侏儒纷纷向着这处蜂拥而来,看似不经意的步履迈动间却隐透着杀戮气息。以多欺少历来就是地行族最钟爱的对战方式,此时此刻,部分急于邀功之徒已经隐蔽地抽出了刮刀,硕大而妖异的眸子里凶芒冷耀。
“调戏撒迦大王的老婆,就好比是调戏老子的亲娘!他妈的,我倒是要看看这小胖子想怎么死!”当先围拢过来的百余名侏儒当中,一个压抑的声音低沉咆哮起来,很快便引发了大量同族的附和。
每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戈牙图与撒迦之间的关系,远非前者自吹自擂的师徒那么简单。善于察言观色的地行族人早在摩利亚时就已经发现,他们的王在面对那黑发年轻人的时候,往往会显出异样的畏惧情绪来,尽管那是掩饰在一贯油滑外表下的。
于是“大王”这个颇为滑稽的头衔,便在私底下逐渐成了地行侏儒对撒迦的统一称谓。王是无可取代的,但在侏儒们的心里,王所敬畏的对象无疑更加值得巴结。
然而紧接着传来的对话,却让所有这些“满腔忠勇”的拍马者从天堂直接跌倒了地狱。
“如果不喜欢这些条件,我拿一大块领地和你换这个小妞怎么样?光明神在上,她可真是个尤物!”衣着华贵的汤姆森虽然是在和撒迦说话,但一双嵌在**中的小眼却始终粘在罗芙身上,只差没流出口水来,“你考虑考虑,实在不行,再多加点钱也可以。斯坦穆是个讲法制的国家,任何事情都好商量,就算买卖不成,交个朋友总行吧!”
罗芙紧蹩的秀眉间已经在蕴育着风暴,撒迦却始终神色如常:“十分抱歉,我对你所有的建议都没什么兴趣。”言语的同时,他淡然直视正在人群中垫脚张望的戈牙图,后者立时低声吼出几句地行土语,四周涌来的侏儒均表现得有些悻然,但还是迅疾四下散去。
“这样的话......那没办法了,真是可惜。”汤姆森白白净净犹如剥壳鸡蛋般的脸庞上略现失望之色,依依不舍地看了罗芙几眼后,策马行远。那些穿金饰银的随从也是满脸憾色地随之而去,一路劝慰着主人,浑然不知已是悉数在鬼门关上兜了个圈子。
“蒙达,什么事?”雷鬼急匆匆地从前方折返,妖异的红眸顾盼着四处。
“一个无聊的贵族而已。”罗芙恢复了冷漠的神色,怀中化为茧状的红正随着呼吸而微微颤动着,仿似柔弱的婴儿。
“不算太坏的贵族......”撒迦笑了笑,举步跨入官道上陷落的又一个巨坑,“索尼埃那边,怎么样了?”
“都已经进了城,小部分侏儒也到了城下,等着您的吩咐。”雷鬼简练地回答。
撒迦不置可否地点头,直视着前方地面上逐渐升起的陡坡,缓慢地举步,一分分行上坡顶。
广袤无际的原野中央,一堵由粗糙麻石砌垒而起的城墙,就这样突兀而倨傲地出现在他视野里,巍峨屹立。这一眼望去竟似难以触及尽头的高墙,宛若某种阻隔着生与死的奇诡神迹,墙的那端是人间,而这头则是地狱。
数以十万计的难民构筑了这幅沉暗画卷中唯一的动态,所有卑微的、平凡的、富有的,或是曾经高高在上的生命,都犹如发了疯般在污浊泥浆中彼此推搡,甚至践踏。妇女和孩子的哭泣声夹杂着男人们声嘶力竭的粗口,在涌动跌宕的潮头间此起彼伏,闷动若雷。
此时的旷野,没有风。
城头上高挑的斯坦穆国旗与巴帝军旗,俱是静静垂悬,仿佛与那些神情冷峻的守军一般,漠然注视着城外汹涌的人潮。那垛口间大张机簧的劲弩和引弦待发的强弓,尽皆毫不掩饰地对向下方,确保着逃生的规则得以被完美遵守。
所谓规则,就是所有难民眼中的那扇城关偏门,以及围绕着那处展开的厮打争夺。每次窄门拉开,只能有两名遍体鳞伤的幸运者进入,试图验证自身运气的贸然者都被门后守伏的长柄刺枪扎得对穿,血淋淋地抛出,于是本就接近绝望的颗颗心灵逐渐变得更加疯狂。
十余里开外的半边天空已愈发炽烈火红,但原本隐约可闻的厮杀微声却逐渐消失。每个难民都知道,这意味着又一批守护者在蛮牙人的利爪下全军覆没,那些咀嚼着人体器官的恶魔,很快就会攻来了。
“蒙达,我该怎么跟那些侏儒说?”雷鬼犹豫了很久,还是低声开口问道。混乱不堪的环境使得他感到了些许忐忑,而始终在皱眉沉思的撒迦,却让内心中不安定的因素隐隐加剧。
鱼人从来没有看过撒迦脸上出现过如此凝重戒备的神色,更加不明白的一点,却是对方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去看那扇人人注目的偏门,反而面向后方,远眺着来时的道路出神。
“你告诉他们,等,等到苏萨克找到内应为止。”撒迦拉低了蒙覆的头罩,微不可闻地道,“冲开主城门不是件难事,但我现在还没打算这样去做。”
雷鬼沉声应了,转身疾步行远。俏立在一旁的罗芙似是也觉察到撒迦的异样,悄悄地伸过手来,却是不由怔住:“你的手好冷,怎么了?”
撒迦摇了摇头,并未答话。
他的目光,正由近及远地在黄褐色的平原上掠过,只是在触及那些直径超过三丈,每隔二十丈左右便会相继陷入地面的深坑时,会短暂停留。
一路上撒迦都在注意着这行分布极有规律的巨大坑体,它们看上去像是沉重的攻城楼车在停止前行时留下的印痕,在半途中突兀出现,如今又在城墙不到半里的地方无声消失。
不知不觉间,撒迦的瞳孔缓缓收缩了一下,刹那间竟是有若钢针。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所有这些残留着强大能量波动的深痕,其实是某种巨灵的足迹。
撒迦无法确定这头直立行走的大家伙究竟是什么,却隐约觉得,就在此时此刻,它可能正蛰伏于平原某处用世上最大的眼睛注视着这方。
而他却不能看到它的身影。
斯坦穆不比其他大陆诸国,行省之间的交界处往往存在着极为辽阔的平原草地,渺无人烟。惯于迁徙的游牧民族自然不会认为距离是个问题,但是相对于沦为难民的他们而言,双腿已经成了最后还能依靠的东西。
所有从北部逃出的难民当中,很少还有人能留下马匹或是别的什么牲畜。从财产到勇气,这场战争几乎耗尽了斯坦穆人的一切。
战火就在后方十余里的城池内熊熊燃烧,随着风势自北而来,逃亡中的人们仿佛再次嗅到了那股浓烈的血腥味。不算太长的日子里,从边境直到国家中部,一个又一个行省被相继攻破。愈卷愈是庞然的难民浪潮由最初的数千不到逐渐扩展为十万有余,行动迟缓的同胞都变成了蛮牙人腹中的美食,于是幸存者们也就更加惶恐失措,宛如一群盲目奔逃中的牛羊。
巴帝主力军队的反攻,使得蛮牙锋线的推进速度开始转缓。几番鏖战之后,希斯坦布尔便成了分隔斯坦穆南北端的最后屏障。一边是尸骸遍野的死地,一边则是处在惊惧气氛中的战栗家园,没有人能预料希斯坦布尔什么时候也会变成一堆焦桓废墟,但绝大多数北方难民赶往的首选避难所,赫然便是这座孤独屹立在战线前沿的行省。
突兀回拢的地势与草原上盘旋斜戈的运河,注定了希斯坦布尔成为去向国家南部的必经之地。很多身处不同行省的远亲在逃亡途中相遇,在感叹命运反覆无常的同时,其中部分豪绅家族便结成规模较大的队伍同行。即使是到了如此凄凉窘迫的境地,他们依旧还竭力保持着贵族做派,那些已不多见的马匹和满盛着金银皮裘的行囊,也从另一个方面令他们的自视更高。
已经极少有人能剩下些什么了,穷鬼们甚至连每顿饭的着落都难以寻获。在延绵无尽的难民人流中,像这样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逃亡者占了八成以上比例。他们携家带口,茫然随着身边人群迈动脚步,逆来顺受的本性让各种负面情绪都保持在理智的水平线下。同为难民,穷人唯一还在乎的就是能不能活下去,仅此而已。
苏萨克的残党和地行族人,也悉数混在浩浩荡荡的逃亡大军里,向着希斯坦布尔的边关城门进发。早在离开驻地的时候,索尼埃就已经下令舍弃了所有马匹。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他都不觉得再次拒绝撒迦的建议是个明智举措。
事实上那名并不善于言辞的年轻人偶尔提出的观点往往直接而有效,正因为如此,索尼埃才会直到今天还处在深深的悔恨之中——如果在早些时候不那么刚愎自用,或许现在那些粗豪部下都还活得好端端的,就像以前那样。
解下武装与红巾的苏萨克,看上去和普通人并没有明显的不同。三五成群混迹于人流里的地行侏儒虽然稀稀拉拉延伸了将近数里的范围,但他们才是撒迦心中真正担忧的症结所在。
由于种种必须去考虑的安全因素,希斯坦布尔的城关只开了一道偏门。狭窄的出入空间配备着极之森严的警戒盘查,明晃晃的刀枪环侍下,每次得以通过城门的难民数量,不超过两人。
十个,一百个,甚至是一千个地行侏儒从城关守军眼前经过,或许都不会引起过多的注意,但撒迦需要考虑到的人数,却是整整六万以上。这些草原上并不多见的矮小生灵无法再依靠掘洞潜入,因为眼前的这座行省不比摩利亚帝都,在城墙后面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很可能都已经人满为患。
“在有些特殊的时候,黑暗要比阳光招人喜欢的多。”尽管仍未消肿的嘴唇在说话时有些麻木,全身焦灼的伤处也还在隐隐作痛,但戈牙图的神态却是飞扬跋扈的,“交给我,小子,你会惊讶地发现老师还有很多杀手锏。当然了,我的小豌豆,这只是为你而做。”
默然前行的人群中,一袭黑袍的撒迦微微摇头:“就算是晚上也没有可能,我们得想个别的办法。”
对地行掘进过分旺盛的自信心,让戈牙图一直不认为撒迦正在担心的问题是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缩手缩脚了?我们不需要钻出地面,而是透过土层就能闻出一里以外蹦达的究竟是条精力旺盛的野狗,还是他妈的趴在巷角墙边挨操的婊子!当初不正是因为这个,我和我的族人才能在皇宫里找到你的吗?听我说,最保险的方法是你也一起下到地底去。如果有人发现的话,我想除了普罗里迪斯那样的怪物,这世上不会再有什么东西能在你的手底下保住小命了,不是么?”
撒迦跨出地面上深深凹下的硕大泥坑,空气中弥漫着新鲜土壤特有的腥味,始终在固执地沁入他的鼻端:“如果只有我和你,或许我会按你说的去做。可是现在,我只想能够低调些进城,然后安顿下来,至于你的计划,那恐怕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样说,你应该是有了自己的想法?”戈牙图显得有些泄气。
“让索尼埃和他的人先进去,听说他们能找到些有用的朋友。”撒迦掠了眼后方,那片天空的阴云底部,正闪耀着火一般的赤红,“这是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没有利益的时候,我们最好还是避开它。”
戈牙图思忖半晌,挥手叫过一名诚惶诚恐的族人,接过对方递上的干粮狠狠啃了一口:“好吧,我承认你说得不错。不过话说回来,撒迦,你难道不认为我们的新朋友有点缺乏价值观念?我的老天,他们宁愿随身带上这堆一文不值的猪食,也不肯把那些金灿灿的宝贝儿从山谷里搬出来......”鬼祟地环顾着周围,地行之王压低了声音,“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藏着多少钱,但我发誓,那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得多。”
撒迦略为讶异地看着他:“我以为你最感兴趣的不会是金钱。”
“当然不是金钱,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戈牙图恼怒地低声吼道,“我只想得到那个妞!”
“所以我们得尽快想办法进去,裁决和溯夜一族,可能已经在南边的某个地方了。”撒迦忽转过视线,望向侧方径直行来的一个窈窕身影,“如果你还想活着见到海伦,现在最好找个地方躲起来。”
“为什么?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一位无畏的勇者低头!”戈牙图气咻咻地顺着对方视线望去,立时触上了罗芙投来的冰冷眼神,“呃,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情要做,小子,恐怕我得先离开一会儿了......”
“能告诉我,那天晚上你到底用了什么吗?”撒迦叫住了准备溜之大吉的侏儒。
戈牙图略顿了脚步,不安地回顾着,这几天来他感觉自己像个无力抗拒任何事情的婴儿,而扮演神甫角色的罗芙则用电系魔法洗礼了他的全身:“那小玩意叫‘迷乱水晶’,盐湖盆地的特产。怎么说呢,除了强烈的催情效果以外它没有任何作用。如果你想要,我这里还有很多。”极为暧昧地挤了挤眼,侏儒飞快钻进人群,“不过,我想你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了。”
撒迦苦笑着摇头,直到那熟悉的清香气息逐渐靠近,方才若有所思地转回身,执住罗芙的柔软手掌:“别再为难戈牙图了,他可不会什么魔法防御,迟早会变成烤肉的。”
罗芙的颊边悄然飞起两抹嫣红,先前雌豹般凶悍的眼神已变得羞不可遏:“这下流的侏儒,迟早有一天我会杀了他。”
“你最好还是别这样做,戈牙图是我目前唯一还能找到的老师了......”撒迦半开玩笑的接口。
“喂,年轻人,身边的妞不错啊!大家轮换着玩几天?”后方赶上的马蹄声低促响起,一个体态肥硕,留着细长八字须的青年男子在数十名随从的簇拥下分开人流,驾驭坐骑缓缓行到撒迦旁侧,“放心,我不会白玩的,要钱还是要个官衔你尽管说。等进了城,我保证你能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我们汤姆森少爷可是斯坦穆最大领主唯一的继承人!”几名随从争先恐后地附和着,仿佛早已习惯于应对类似的情形。
撒迦按住了罗芙悄然抬起的右手,微笑道:“如果我不愿意呢?”
四面八方的人群间,无数地行侏儒纷纷向着这处蜂拥而来,看似不经意的步履迈动间却隐透着杀戮气息。以多欺少历来就是地行族最钟爱的对战方式,此时此刻,部分急于邀功之徒已经隐蔽地抽出了刮刀,硕大而妖异的眸子里凶芒冷耀。
“调戏撒迦大王的老婆,就好比是调戏老子的亲娘!他妈的,我倒是要看看这小胖子想怎么死!”当先围拢过来的百余名侏儒当中,一个压抑的声音低沉咆哮起来,很快便引发了大量同族的附和。
每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戈牙图与撒迦之间的关系,远非前者自吹自擂的师徒那么简单。善于察言观色的地行族人早在摩利亚时就已经发现,他们的王在面对那黑发年轻人的时候,往往会显出异样的畏惧情绪来,尽管那是掩饰在一贯油滑外表下的。
于是“大王”这个颇为滑稽的头衔,便在私底下逐渐成了地行侏儒对撒迦的统一称谓。王是无可取代的,但在侏儒们的心里,王所敬畏的对象无疑更加值得巴结。
然而紧接着传来的对话,却让所有这些“满腔忠勇”的拍马者从天堂直接跌倒了地狱。
“如果不喜欢这些条件,我拿一大块领地和你换这个小妞怎么样?光明神在上,她可真是个尤物!”衣着华贵的汤姆森虽然是在和撒迦说话,但一双嵌在**中的小眼却始终粘在罗芙身上,只差没流出口水来,“你考虑考虑,实在不行,再多加点钱也可以。斯坦穆是个讲法制的国家,任何事情都好商量,就算买卖不成,交个朋友总行吧!”
罗芙紧蹩的秀眉间已经在蕴育着风暴,撒迦却始终神色如常:“十分抱歉,我对你所有的建议都没什么兴趣。”言语的同时,他淡然直视正在人群中垫脚张望的戈牙图,后者立时低声吼出几句地行土语,四周涌来的侏儒均表现得有些悻然,但还是迅疾四下散去。
“这样的话......那没办法了,真是可惜。”汤姆森白白净净犹如剥壳鸡蛋般的脸庞上略现失望之色,依依不舍地看了罗芙几眼后,策马行远。那些穿金饰银的随从也是满脸憾色地随之而去,一路劝慰着主人,浑然不知已是悉数在鬼门关上兜了个圈子。
“蒙达,什么事?”雷鬼急匆匆地从前方折返,妖异的红眸顾盼着四处。
“一个无聊的贵族而已。”罗芙恢复了冷漠的神色,怀中化为茧状的红正随着呼吸而微微颤动着,仿似柔弱的婴儿。
“不算太坏的贵族......”撒迦笑了笑,举步跨入官道上陷落的又一个巨坑,“索尼埃那边,怎么样了?”
“都已经进了城,小部分侏儒也到了城下,等着您的吩咐。”雷鬼简练地回答。
撒迦不置可否地点头,直视着前方地面上逐渐升起的陡坡,缓慢地举步,一分分行上坡顶。
广袤无际的原野中央,一堵由粗糙麻石砌垒而起的城墙,就这样突兀而倨傲地出现在他视野里,巍峨屹立。这一眼望去竟似难以触及尽头的高墙,宛若某种阻隔着生与死的奇诡神迹,墙的那端是人间,而这头则是地狱。
数以十万计的难民构筑了这幅沉暗画卷中唯一的动态,所有卑微的、平凡的、富有的,或是曾经高高在上的生命,都犹如发了疯般在污浊泥浆中彼此推搡,甚至践踏。妇女和孩子的哭泣声夹杂着男人们声嘶力竭的粗口,在涌动跌宕的潮头间此起彼伏,闷动若雷。
此时的旷野,没有风。
城头上高挑的斯坦穆国旗与巴帝军旗,俱是静静垂悬,仿佛与那些神情冷峻的守军一般,漠然注视着城外汹涌的人潮。那垛口间大张机簧的劲弩和引弦待发的强弓,尽皆毫不掩饰地对向下方,确保着逃生的规则得以被完美遵守。
所谓规则,就是所有难民眼中的那扇城关偏门,以及围绕着那处展开的厮打争夺。每次窄门拉开,只能有两名遍体鳞伤的幸运者进入,试图验证自身运气的贸然者都被门后守伏的长柄刺枪扎得对穿,血淋淋地抛出,于是本就接近绝望的颗颗心灵逐渐变得更加疯狂。
十余里开外的半边天空已愈发炽烈火红,但原本隐约可闻的厮杀微声却逐渐消失。每个难民都知道,这意味着又一批守护者在蛮牙人的利爪下全军覆没,那些咀嚼着人体器官的恶魔,很快就会攻来了。
“蒙达,我该怎么跟那些侏儒说?”雷鬼犹豫了很久,还是低声开口问道。混乱不堪的环境使得他感到了些许忐忑,而始终在皱眉沉思的撒迦,却让内心中不安定的因素隐隐加剧。
鱼人从来没有看过撒迦脸上出现过如此凝重戒备的神色,更加不明白的一点,却是对方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去看那扇人人注目的偏门,反而面向后方,远眺着来时的道路出神。
“你告诉他们,等,等到苏萨克找到内应为止。”撒迦拉低了蒙覆的头罩,微不可闻地道,“冲开主城门不是件难事,但我现在还没打算这样去做。”
雷鬼沉声应了,转身疾步行远。俏立在一旁的罗芙似是也觉察到撒迦的异样,悄悄地伸过手来,却是不由怔住:“你的手好冷,怎么了?”
撒迦摇了摇头,并未答话。
他的目光,正由近及远地在黄褐色的平原上掠过,只是在触及那些直径超过三丈,每隔二十丈左右便会相继陷入地面的深坑时,会短暂停留。
一路上撒迦都在注意着这行分布极有规律的巨大坑体,它们看上去像是沉重的攻城楼车在停止前行时留下的印痕,在半途中突兀出现,如今又在城墙不到半里的地方无声消失。
不知不觉间,撒迦的瞳孔缓缓收缩了一下,刹那间竟是有若钢针。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所有这些残留着强大能量波动的深痕,其实是某种巨灵的足迹。
撒迦无法确定这头直立行走的大家伙究竟是什么,却隐约觉得,就在此时此刻,它可能正蛰伏于平原某处用世上最大的眼睛注视着这方。
而他却不能看到它的身影。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